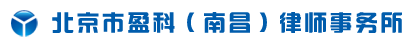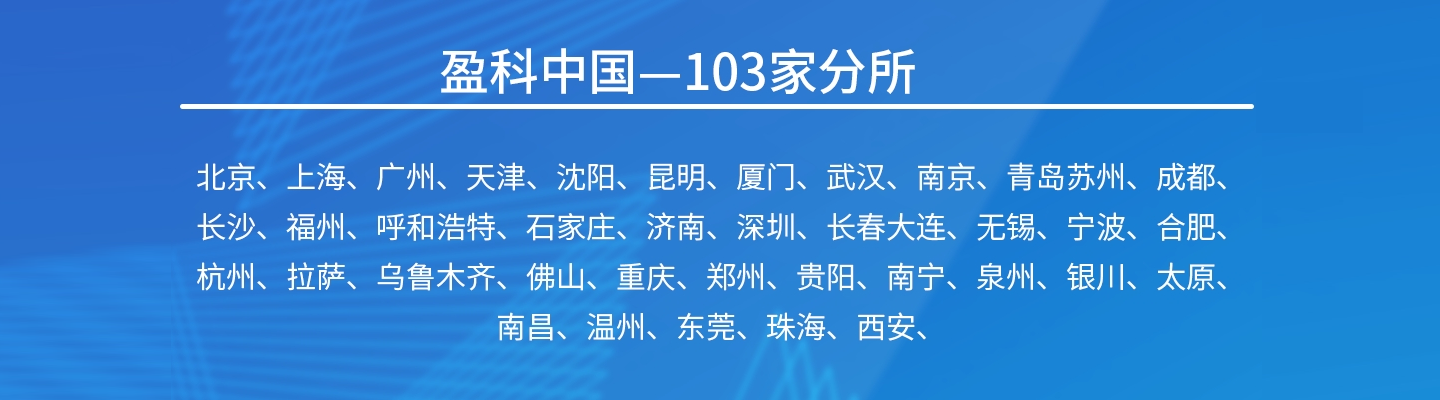周跃飞等人涉黑案辩护词
(这就是我前段时间提到的自认为写的很认真的辩护词,摘发一下涉黑部分。需要明确的是,并不推荐每个案件都写这么长的辩护词。因为法官没时间看,本案的特殊在于连续开庭60多天,这些话都是我当庭说过的,所以写下来权当方便法官检索)
一、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1、本案不具有黑社会罪的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特征。
《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提出:“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从而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一般犯罪集团的关键所在。”因此,辩护人首先谈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特征。
第一,《座谈会纪要》规定的非常明确,无论是非法控制还是重大影响,其入罪的标准是要造成“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结果,但本案没有证据对此予以证明。
第二,关于如何认定“非法控制”特征,最高人民法院第623号指导案例“刘烈勇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提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并非单纯为了实现犯罪而存在,其往往谋求在一定地区范围内或特定行业内形成一种非法的垄断,使正常的社会管理和行业管理制度不能得以运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来分析本案。公诉人的举证仅仅显示了被告人拥有煤矿,并无证据证明当地煤矿存在“正常的社会管理和行业管理制度不能得以运行”的现象,即本案不符合法定的“非法控制特征”。
第三,虽然《起诉书》提及被告人垄断当地煤矿行业,但“垄断”不是一种主观的个体感受,而是客观存在的阻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3条规定:“垄断行为包括:(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以此考察本案,公诉人在举证过程中并未出示涉及市场份额、垄断定价、限制竞争等与认定垄断相关的客观证据。恰恰相反,正如太阳每天都在升起一样,耒阳当地每年也都有大量的符合行政许可条件的境内经营者进入煤矿经营领域,这些实际发生的成功进入案例均有力地证明,被告人所在的煤炭市场并未形成《起诉书》所指控的垄断。
第四,《起诉书》虽然提及各被告人“通过控制基层政权组织的方式为控制经营的煤矿提供保护”,但是本案在案证据显示,所谓的“被控制的基层政权”的所在地与各被告人的煤矿所在地并不一致。庭审过程中提及被告人在红联村有富兴煤矿、鸿盛煤矿、岸金煤矿,但红联村的村支书就是《起诉书》中描述的与被告人早有矛盾的周青华,这个周青华是“谢氏黑社会的马仔”,是本案起诉各被告人的刑事附带民事责任的原告,是在2015年4月21日公然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带人殴打辩护人的逞凶者,如此一个周青华,仅凭逻辑和日常经验就可以认定他不可能为被告人提供保护。公诉人还提及红田煤矿、泗马塘煤矿、大塘煤矿、上和冲煤矿和湘潭联营煤矿,但显而易见的是,公诉人并未举证证明被告人控制了上述煤矿所在地的基层政权。与之相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利用陈志兵控制泥湾村,但各被告人在泥湾村没有煤矿。至于本案被告人付忠群所在的陶洲村,本案证据显示,付忠群于2008年当选村干部,同年与蒋方林发生不合,导致蒋方林、付忠群两人均在2008年当年就退出陶洲村的煤矿经营,这显然也不具有所谓付忠群为蒋方林提供保护的客观可能性。简言之,本案被告人的绝大部分煤矿所在地根本没有所谓的被控制的村干部,而公诉人指控的被控制的村干部所在地则没有被告人的煤矿,这种煤矿地点与村干部地点的背离,证明了本案不可能存在“通过控制基层政权组织的方式为控制经营的煤矿提供保护”的情形。
2、本案不具有黑社会罪的经济特征。
《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提出:“黑社会的主要犯罪目的就是获取非法经济利益,认定黑社会经济特征的核心就是审查资金的去向。”全国人大法工委对黑社会经济特征的立法释义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以黑促商,以商养黑’的循环过程。”
依据上述规定审查本案,仅凭《起诉书》就可以认定本案不构成黑社会犯罪。
第一,关于“以黑促商”。《起诉书》指控的强奸、抢劫、贩卖毒品、容留卖淫、赌博、开设赌场、非法拘禁都是非组织犯罪,即无论这些罪名是否成立,以及是否获得利益,均与黑社会的认定无关。
聚众斗殴、故意伤害第2、6、7、10起,寻衅滋事1、2、5起,非法持有枪支,非法买卖枪支虽系《起诉书》指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为了组织利益而共同实施的组织犯罪。但考察这十项指控,聚众斗殴的沙场不是各被告人的财产,各被告人也未通过聚众斗殴获得沙场的所有权;故意伤害第2、6、7、10起,公诉人的证据只证明存在人身伤害,而并无获取非法经济利益的相关内容;在非法买卖、持有枪支问题上,公诉人证据没有与获取非法经济利益有关的内容;寻衅滋事第1起的泗马塘煤矿与东资煤矿纠纷,被告人虽然获得资金赔偿,但这笔资金赔偿系在当地人民法院主持下获得的,除非该人民法院系黑社会保护伞,否则这是合法收入,同时据耒阳市国土部门的确认,此次纠纷系东资煤矿非法越界盗采被告人的合法矿场资源所引发的,该笔赔偿也是针对东资煤矿的越界盗采行为对被告人合法财产所造成的损失所作出的依法赔偿,并且该赔偿远低于被告人合法财产的实际损失,各被告人在寻衅滋事第1起中非但未获得非法经济利益,反而存在经济损失;寻衅滋事第2起的刘显波与资春明纠纷,《起诉书》明确记载刘显波不是黑社会组织成员,因此无论刘显波在此次纠纷中是否获得经济利益均与本案是否构成黑社会犯罪无关,同时依据《起诉书》记载,刘显波只是事后联系周跃飞,并无向周跃飞提供经济回报的相关描述,本案证据亦无刘显波向周跃飞进行利益输送的证明内容,因此寻衅滋事的第2起也不支持各被告人的行为具有获取非法利益的情形;寻衅滋事第5起的周后会拆迁纠纷,《起诉书》中没有各被告人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相关指控。简言之,各被告人所拥有的个人财产,没有一分钱是通过《起诉书》所指控的组织性犯罪所获取的,即被告人的财产全是合法财产。
此外,《起诉书》虽称各被告人通过非法手段抢占煤矿资源。但是,到底哪家煤矿是被告人通过非法手段抢占的?《起诉书》没有提及任何具体事实基础,公诉人亦未予以举证。《起诉书》还称被告人非法涉足房地产、宾馆行业。但是,关于被告人到底采取了何种非法手段来涉足房地产和宾馆行业,公诉人也没有出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
由此可见,本案不存在丝毫的“以黑促商”的犯罪情形。
第二,考察资金的去向,本案也不存在“以商养黑”的情况。《起诉书》指控各被告人“以商养黑”的方式主要是所谓的“为小弟租房子”、“提供娱乐机会”、“资助外逃”“花钱探监”“买通关系提前出狱”五种。然而,在案证据显然不支持公诉人的指控。
首先,被告人到底租了哪里的房子、到哪个消费场所消费?没有相关证据。不但没有租房协议、现场指认、消费凭证等客观证据,甚至在被告人笔录中也没有与租房、娱乐消费有关的具体陈述。至于所谓周跃飞资助蒋荣华等人在周青华事件中外逃,公诉人提供的同步录像就已经证明,有关内容完全是侦查人员编造笔录,用侦查人员自己的话冒充周跃飞的供述。
其次,虽然公诉人指控本案被告人帮助谢满成、曹华古出狱,但是辩护人提醒合议庭注意的是,二人出狱均履行了合法程序,并有合法的司法文书,如果公诉人强行要说二人的出狱是所谓的“买通关系”,那么公诉人首先应当证明到底是哪个腐败的司法人员参与其中。在未证明存在腐败官员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出现花钱出狱的结果的。
再次,关于大哥看望小弟的指控,除谢满成认可作为侄子的周方毅因谢母去世而来监狱告知丧讯,以及梁德华认可周方毅因人情来监狱探望一次之外,其他被告人均当庭否认。辩护人提醒合议庭注意的是,证明探望存款是非常容易的,因为监管机关收取存款必须依法建立长期档案,然而对于如此可轻易取得的证据,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却并未出示,由此可见,所谓大哥探望小弟的指控完全是不成立的。
最重要的是,《座谈会纪要》关于所谓的“以商养黑”的认定标准,是指组织资金足以维持组织的稳定和发展,但据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显示,谢满成、梁德华均只接受过一次探望,接受探望款项总计不过千元,甚至就算是把真实性抛开不谈,将公诉人提到的所有的所谓被探视的小弟全加在一起,公诉人所指控的涉案探望金额也不过区区万元。如此吝啬的一点小钱,怎么可能让本案各被告人如《起诉书》所指控的自2000年成立黑社会,横行十余载,获取亿万财富呢?这完全是违背常识的,不具有任何的逻辑性和合理性。
第三,“经济特征”是指某人或者某机构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资产。证明被告人“以黑促商、以商养黑”的证据应当是经营记录、收入与支付凭证等客观证据。本案中,各被告人的真实的客观资产是多少?各被告人的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如何区分?黑社会组织的组织财产是什么?公诉人均未予以举证。
以公诉人罗列的股权登记资料为例。这些资料包含周跃飞入股农村信用社的证据,那么这个农村信用社是否属于涉黑财产?认定是否涉黑的依据与理由是什么?公诉人没有任何说明。
此外,公诉人将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比例乘以注册资金即得出被告人资产的数额。但显而易见的是,公诉人的这种举证方式是毫无经济常识的。众所周知,注册资金仅代表企业进行工商登记时的静态数字,但随着企业的经营,这个数字可以随时发生动态变化,可以增值,也可以贬损。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开的《衡阳国企改制战略解读》一文显示:“衡阳生产的柴油机、拖拉机、自行车、手表、啤酒、毛纺与棉纺制品等等,曾经走俏一时。但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衡阳老工业陷入了困境,大量国有企业连年亏损,资不抵债,连衡变、衡啤、古汉等优势企业也举步维艰。到2003年底,全市357家市属国有、集体企业总资产87.1亿元,总负债102.8亿元,整体账面资产负债率高达118%。”显而易见,这些负资产的国企股权不再等同于注册资金,拥有这些股权不仅不代表财富,反而是负担。以此来考察本案。被告人的企业已经注册多年,其资产是增值了还是贬损了?公诉人没有进行举证。
总之,辩护人认为,经济特征是一种客观存在,证明经济特征的证据链条应当是:1、证明存在客观资产;2、证明客观资产的准确数额;3、证明资产属于被告人;4、证明资产系通过黑社会手段获取;5、证明资产用于资助犯罪活动;6、证明资产数额达到入罪标准。但纵观全案,公诉人的举证连第二步都没有做到。
3、本案不具有黑社会的行为特征。
关于行为特征,公诉人主要是通过整合个罪来间接证明各被告人涉黑。但是辩护人认为,此种证明方式本身就是逻辑错误的。个罪是独立个体实施的独立行为,不同于有预谋的组织行为。在本案的个罪举证过程中,公诉人并未针对个罪是否具有“受组织指挥、为组织谋利”的事实进行举证,即公诉人根本没有就个罪是否属于组织性犯罪进行举证,因此,即便个罪成立,本案还是不能认定黑社会罪的成立。
此外,《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为了显示自身的实力而于2004年在泗马塘举办枪展,但是关于被告人到底展示了什么枪?展示了几把枪?枪展参与人是谁?枪支来源是什么?《起诉书》均无具体事实陈述,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也放弃了对此项指控进行举证。此处辩护人提醒合议庭注意,无举证就无认定,这是《刑事诉讼法》最基本的证据裁判原则。并且,泗马塘地处偏僻,除了矿工,人迹罕至,如果被告人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展示枪支,根本就不会有人看到。行为模式与行为目的完全相悖,可见《起诉书》的指控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起诉书》指控的持有和买卖枪支行为全部发生在2008年之后,由此可见,被告人不具有在2004年举办枪展的客观可能性。
再有,《起诉书》认定各被告人实施的组织犯罪造成两人死亡,但是纵览《起诉书》,只有聚众斗殴的指控中提到了两人死亡,并且《起诉书》清楚地认定了此二人的死亡并非各被告人所为。《起诉书》自相矛盾,竟然将他人造成的伤害结果张冠李戴到各被告人身上。即便是聚众斗殴这种双方均有过错的罪名,也是需要分清各自责任,实现罪责刑相一致的,但公诉人用他人的犯罪结果来人为加重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其心之毒,跃然纸上。
至于公诉人超出《起诉书》的指控内容而自行举证的周罗生故意伤害事实和红田煤矿竞标事实。首先,周罗生本人的笔录陈述自己没有被打、只是家中物品被砸。但谷任冬竟说将罗打晕,谢新珠则说用木棍打了几下但没有晕,谷茂新说谢新珠虽然到打现场但并未打人。简言之,公诉人的举证已经自证了其指控错误。其次,在红田煤矿竞标案中,公诉人明明知道此次竞标系由当地人民政府主持召开的一个资源招标活动,整个招标过程均有人民政府的工作记录,但是公诉人却对如此客观真实的证据不予取证,而是只出具被告人的主观陈述,称谷任冬瞪了几眼就吓得蒋炳威再不敢竞标。并且,此次竞标的起拍价只有10万元,然而被告人却花费了59万元才竞标成功。如果谷任冬瞪眼就能吓退竞争对手,被告人又何必溢价六倍才竞标成功?这显然毫无逻辑的。
最后,即便不考虑公诉人在证明方式上的错误,辩护人认为,公诉人关于黑社会行为特征的认定同样缺少法律依据。本案的全部寻衅滋事指控不是矿产纠纷,就是房屋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出版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的指导意见:“一些公民因民事纠纷或个人恩怨在公共场所殴打、辱骂他人,在路上拦截、追逐他人,或为索要债务而强行拿走、毁坏、占有他人财物等行为,虽然在行为方式上与寻衅滋事犯罪相似,但都是事出有因,没有无事生非、寻衅滋事的动机,一般就不能作为寻衅滋事罪处理。”由此可见,本案的所谓寻衅滋事,全部事出有因,并未被告人无事生非,不应当作为寻衅滋事予以处理,自然也就不成为黑社会的行为特征。
4、本案不具有黑社会罪的组织特征。
对于如何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在第619号指导案例“邓伟波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指明:根据《全国人大常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一款的解释》的规定,组织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不具备这一特征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我们认为,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和把握:(1)审查犯罪组织的目的性。普通共同犯罪同样有可能成员众多,纠集时间长,但普通共同犯罪的目的是实现组织成员个人的目标和利益,而黑社会犯罪的目的在于维护其组织的利益,是为了组织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最终实现其对一定区域或行业的非法控制。(2)审查核心成员的稳定性。黑社会组织外围成员可能更换,但组织头目、骨干成员是相对固定的,相互之间联系紧密。(3)审查犯罪组织的纪律性。普通共同犯罪是依靠成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对成员个人的行为,尤其是实施犯罪活动之外的行为,不会进行干涉。而黑社会组织有其组织纪律和活动规约来确保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4)审查分配机制。普通共同犯罪一般在每起具体犯罪后直接“坐地分赃”,黑社会组织一般会有相对稳定的分配模式,组织成员的收入与各自在组织中的地位成正比。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案例中提出的四点认定依据来分析本案。
第一,本案无法证明组织的形成。公诉人在“组织形成”部分只举示了被告人口供,但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并且这些口供又彼此矛盾,那么依据口供补强原则,公诉人未完成对组织形成的举证责任,即本案无法证明各被告人曾经组织黑社会的相关事实。
此外,即便只分析被告人供述,各证据之间亦是相互矛盾。公诉人指控各被告人于2000年通过电话联络而召开家庭会议并决定成立黑社会组织。但事实上,2000年的时候各被告人根本不具备通讯工具,不具有电话联络的客观可能性。辩护人注意到,公诉人称有通讯公司证明大义乡有部分村民于2000年拥有手机,但显而易见的是,有村民拥有手机不等于被告人拥有手机,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辩护人还注意到,公诉人称蒋方林家和富兴煤矿拥有座机,但是,除非所有参会人在电话联络的时恰好全都身处这两地,否则,仅通过蒋方林、富兴矿的两部座机就召集到被告人到场是不具有客观可能性的。那么考察本案在卷证据,《周跃鹏2012年11月30日笔录》记载:“周方毅逃到蒋方林家,并给我打电话。我接了周方毅的电话,就和周跃飞从家里出发,赶到蒋方林家,这时我大哥周梓奇已经到了。”《周梓奇2012年11月10日笔录》记载:“2000年4月,周方毅给我打电话,说蒋方林让我通知家里人一起开会。我就给周跃鹏、周跃飞打电话,让他们去蒋方林家。”《周跃飞2012年11月23日笔录》记载:“2000年5月,我接到蒋方林电话,我接到电话就和周跃鹏、周方毅一起来到蒋方林家。”综合上述证据,周跃飞、周跃鹏、周梓奇都说事发时人在自己家中,并不是在有电话的富兴矿,并且周梓奇早已分家单过,与周跃飞、周跃鹏不在一处,由此可见,他们三人是不可能接到电话的。另外,关于电话联络的顺序,周跃鹏说在家中接到周方毅的电话,然后与周跃飞一同到蒋方林家。周梓奇则说自己在家中接到周方毅的电话,然后再由自己给周跃鹏、周跃飞打电话。周跃飞则说蒋方林给自己打电话,然后自己与周方毅一同到蒋方林家。各被告人之间的陈述完全矛盾,事实不清。
并且,即便是如此矛盾百出的被告人供述,各被告人亦均当庭否认曾经召开过家庭会议,称关于召开家庭会议的庭前有罪供述均系刑讯逼供下的违心供述。关于非法证据问题,辩护人此处不赘。辩护人需要提醒合议庭注意的是,《周跃鹏2012年11月14日笔录》记载:“2000年底,我回到富兴煤矿,帮我大哥管事。”蒋方林的妻子周龙香在《2012年12月26日笔录》记载:“侦查人员问,2000年5月周跃飞、周跃鹏、周梓奇、周方毅到过你家吗?周龙香答,周跃飞、周跃鹏二人在外打工,不在耒阳,所以他们没来过我家。”可见,在公诉人指控的会议时间内,周跃鹏、周跃飞是有不在场证据的,这也佐证了所谓召开家庭会议的指控是不真实的。
关于成立黑社会的原因。周方毅在《2012年12月31日笔录》称谢冬根要借用采矿许可,周梓奇不同意。谢冬根为此经常找各被告人的麻烦,所以各被告人准备对付谢冬根。而《周梓奇2012年11月18日笔录》则记载:“谢文生要在我们矿区采煤,我们不同意,谢冬根为此经常找各被告人的麻烦。”这里,纠纷原因从借用采矿证,直接变成了谢家一方越界采矿。但是,到了蒋荣华的《2012年10月30日笔录》则说,周家与谢家争夺观山坳煤矿,所以两家发生了矛盾。这里,周、谢之间的所谓矛盾又从谢家越界采矿变成了周家争夺谢家的观山坳煤矿。此外,再据周跃鹏的《2012年11月10日笔录》和《2012年11月30日笔录》记载,谢冬根砍伤了周武文的父亲,为了报复谢冬根,所以大家召开会议。周跃鹏的这个陈述首先与其他被告人的陈述相互矛盾,同时,周跃鹏、周梓奇、周跃飞、周方毅、蒋方林五人与周武文非亲非故,何以要为一个毫不相识的人去实施砍人这种严重犯罪行为呢?这显然有违常理。由此可见,对于成立黑社会的原因,各证据彼此矛盾,无一对证,完全事实不清。
关于黑社会的形成过程。所谓“形成”,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但是,无论是《起诉书》认定的指控事实还是本案的在卷证据均证明,2000年5月发生周青华事件之后,周方毅、杨中永等人外逃并随后被捕入狱,不具有形成黑社会的客观条件。周跃飞、周梓奇、周跃鹏、蒋方林等人在2000年之后则没有任何与黑社会有关的行为,没有行为,何来“形成”黑社会?
这种没有任何行为的时间空档一直维持到2006年前后,《起诉书》突然就认定所谓谢氏黑社会被打掉之后,各被告人的黑社会出现大发展。那么这里的问题是,既然被告人在2000年后根本没有与黑社会有关的行为,那么2006年从天而降的黑社会的来源是什么?这个莫名其妙出现的黑社会出现了何种大发展?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上述诸多违背常理、不合逻辑的疑问,本案均无合理解释。
第二,没有证据证明各被告人之间存在“稳定的分配模式”。公诉人未对“稳定的分配模式”进行任何举证,各被告人即不需要缴纳组织经费,也不存在组织向各被告人进行利益输送。同时,《起诉书》记载的很清楚,赌博、抢劫等可能获得经济利益的行为均不是组织性犯罪,组织性犯罪又全都与获利无关。《起诉书》所谓的安排小弟统一食宿,各被告人均当庭否认,公诉人也没有提供可以证明各被告人安排小弟统一食宿的相关证据,没有租房协议,没有与租房有关的现场指认材料。这一点,前文已有分析,此处不赘,即本案不具有分配模式的相关情形。
第三,本案没有统一的行为目的。黑社会的行为目的是维护组织的稳定、发展,最终实现非法控制。但据《周梓奇2012年11月18日笔录》记载:“2001年开始,蒋方林、周跃飞、周跃鹏我们就分开了。”《周方毅2012年12月9日笔录》记载:“我去坐牢,家里人没有合伙做生意了,各自做事情。”《蒋方林2012年12月28日笔录》记载:“各自有了产业,也没多少兼顾了。”各被告人关于各自分开的陈述是稳定且一致的,公诉人出示的被告人财产信息证据也佐证了各被告人的陈述,这些客观证据明确证明各被告人分处不同行业,各自独立经营,并无统一行为,不符合法定的黑社会特征。
第四,本案没有统一的组织纪律。《起诉书》称黑社会的组织纪律要求小弟要绝对尊重大哥,但《起诉书》又称周跃飞在赌博过程中输给付忠群等小弟几百万,赌博的组织者谢申文也当庭认可此事实。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逻辑上的悖反。如果《起诉书》指控的组织纪律是真实的,那么“小弟”怎么敢赢“大哥”的钱?而如果“小弟”敢赢“大哥”几百万是真实的,那么所谓的组织纪律显然是没人遵守的。还有,组织纪律要求定期召开成员会议,但是在案证据中没有任何被告人定期召开成员会议的相关内容。《起诉书》将一些显然没人遵守的东西称为“纪律”,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总结
综合上述分析,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起诉书》的指控在“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组织特征”四方面无一成立,因此辩护人认为本案不满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犯罪构成,本案指控不成立。